再戰最新的老把戲:「穿越-正義:科技@潛殖」中的反烏托邦動機(dystopia motif)
Author: 許諾丘, 2018年10月27日 23時23分
評論的展演: 穿越−正義:科技@潛殖

〈南榕的二三事〉
更準確地以政治為主題的話,這幽微之處是一個尚未以任何明確形式作出承諾的所在,但卻朝向一種生態式政治觀點下的共活而發生,就是共同生活(政治生活)中「未來正義的所在」,但必然不在現有「正義 /不正義」的二元框架內,而是作為框架外、 又並非烏托邦的「第三項」。這第三項的發生與生成是一種充滿反身性與關係性的調研、思考與實踐的過程,它面對的正是無法以任何特定歷史階段或體制類型來界定的「殖支配」,也就是在人類歷史中一直發生的「潛殖」,「潛殖」這個一直發生也一直被以不同的問題意識來解決(迴避)的關係性問題,就在全球試驗各種民主體制的可能後具體化地呈現在我們的現實關係中:即科技 @ 潛殖。——「穿越−正義:科技@潛殖」策展論述
反(dy-)而不反(anti-)的逃逸路線
一想起反烏托邦(dystopia),三本經典著作——《我們》(1924)、《美麗新世界》(1932)、《一九八四》(1949)——所創造的世界就會浮現眼前,儘管各自對於處於烏托邦世界的家庭功能、情感關係等想像有所差別,但在此等世界中,科技作為關鍵變因,同樣促成了秩序及實用性的極大化,並一次性的改變了從自然環境、經濟活動、社會規範到道德及心理狀態等所有組成。薩米爾欽(Evgeny Zamyatin,1884–1937)想像的建築物或許是所有反烏托邦敘事最貼切的明喻及暗喻:所有的建築物都是由玻璃及透明材質建造而成,所有的動作都是永遠可被觀察、邀請觀察的(constantly visible)。
如果將更多作品列入討論,反烏托邦敘事中對於個體能動性的想像將會更明顯。在2013年出版的《消失吧,紙本世界!》(Die Scanner)中,Martin Schäuble虛構了一個2010年出生的Robert M. Sonntag,以第一人稱描寫了在最後一次大戰後的世界,這個在「超網巨擘集團」子公司——掃描股份公司(註1)——以圖書經紀員一職維生的年輕人如何發現了圖書互助協會(Büchergilde),並如同《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1953)中的主角Montag一樣遭遇了重新認識已知世界的分娩痛楚。1953年的星期一與2013年的星期天——一甲子之距或許改變了故事中當權者以什麼樣的名義銷毀知識,但包括上述三部曲在內,一直以來,反烏托邦小說的公式卻非常固定:原先主角一定是個融入該世界價值觀的平凡人,直到他有機會接觸了「外面的人」,小說中通常會具現為被棄的區域或地下活動,但實際上這裡「外面」的作用是取消了烏托邦世界中的constantly visible,他們不透明的動機及價值觀挑戰了主角一直以來對掌權者及科技的全權信任及依賴,因此當機、停擺。當個體再次有動作,儘管幾乎在所有上述小說中都是悲劇(自殺、處刑、最慘的是《我們》中主角被動了手術,認為自己之前都是有病的幻想)結尾,但至少,因當機而被激起的懷疑論使他能重新調校行為模式及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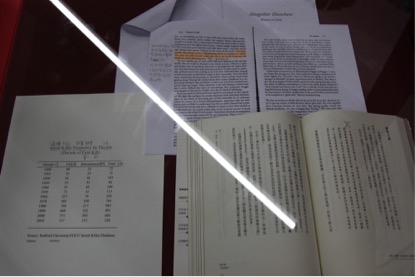
張紋瑄〈國際自殺大賽〉局部
之所以以反烏托邦小說起始,是為了理解「穿越−正義:科技@潛殖」這個如同四方密碼的展名組成。「穿越」、「正義」及「科技」是三個娛樂產業、政治人物及新聞媒體經常使用、以至於對閱聽眾而言除了字面意義不再有任何異義的字眼,「潛殖」(paracolonial)這個字相較陌生,但對一般民眾而言仍可以用對「殖民」一字的認識基礎拼組可能的含義,因此,最令人困惑的反而是三個符號:「−」、「:」、「@」。在策展人黃建宏的完整論述中,「−」的使用是將其作為一種「複合性、動態化的『思辯』(speculative)關係」;「@」則同時帶有這個符號原初在速度及交易(at a rate of)面向上的含義,除此之外也有網際網路介面上(如email、twitter等)的使用意涵;「:」在論述中並沒有特別提及,但如果順勢延用上述兩個符號的定義方式,在此或許不應作為A解釋B,而是作為雙向運算的符號在此起作用。在這樣的前提下,每個單一詞彙的定義更動都會全盤改變對展覽的理解:如果「正義」指的並不是政治正確的「正確」,而是朝向未來共同生活的辯證運算;如果「潛殖」指的並不只是殖民的遺緒,而是在特定時代之外、國與國關係之外、殖民母國消失之後仍然存在的支配關係,那麼,這個展覽意欲處理的就不是為了呼應現下轉型正義政策的配套文化產出,也不是為了呼應數位時代及科技藝術熱的議題消費,而是如同反烏托邦小說作者使當下問題話的處理,同時也呼應了黃建宏給這檔展覽的「獨立書店」比喻,並延續了策展人在其策展實踐中對藝術家個別創作方法論的強調:你們都覺得正義及科技在現在都沒問題、或是「正在變好」,但並非如此——這裡有一些不透明的人正在不透明地這麼思考世界,你可以參考看看。
What if…If only…If this goes on …
在「穿越−正義:科技@潛殖」一展中,由書寫公廠與鄭南榕基金會協同策劃的〈南榕的二三事〉,及位於一樓長廊由超什錦小組及張永達製作的〈媒介翻譯〉可以說為整場展覽、以及短版策展論述提供了最佳補遺。前者暗示了上述強調個體能動性及方法論的取向,五個OA櫃中來自鄭南榕獄中日記及手稿的檔案,要求打開抽屜的觀眾主動的透過檔案重新將已被英雄化的角色組構為人;而後者則透過年表及關鍵科技物的視覺轉譯,讓科技與歷史——及顯而易見在此間的支配關係產生回聲。Neil Gaiman在談《華氏451度》時他說,有三種句型讓作家得以描寫尚不存在的世界:「倘若⋯⋯會如何」(What if…)、「假如⋯⋯的話」(If only…)及「照這樣下去⋯⋯」(If this goes on …),事實上,本展展出的作品——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參展藝術家的創作方法及其能動性的錨定位置——也能以這三種句型被重新被結構。

陳界仁〈十二因緣 — 思考筆記〉中由20到21世紀幾秒間過渡,應是整場展覽最反烏托邦的幾個影格
「倘若⋯⋯會如何」(What if…)的假設句型所要求的是在分析當下之後,對於出路的可能想像,且該想像是在現在進行式而非未來式行使,張紋瑄的〈國際自殺大賽〉重看1980年代末的「自殺」潮,透過調整歷史事實之時也會一併調整歷史詮釋的交互關聯,暴露歷史書寫的政治性;徐坦行之有年的「關鍵詞實驗室」強調在字義之外,該詞彙在當下社會的實施及對實施的具體表述,而他每次調研對象作為「社會」切片也不斷重新定義關鍵詞,本次〈水,地−地盤〉展出數本關於土地的法典以及他對廣東蜑家人的調研紀錄;黃漢明(Ming Wong)的〈明年〉諧擬了雷奈的〈去年在馬倫巴〉(1961),原先影像及對白間複雜的互文在交疊了上海及由Ming Wong一人分飾多角的影像之後,殖民及性別加入了文本遊戲;陳界仁以〈中空之地〉揭露並具現了金融/科技資本主義全控下的個體處境,而在「名字沒了怎麼辦?」的提問聲中,〈星辰圖〉中陳界仁在他哥哥房間中拍到那些「全球監控」、「觀」、「邪惡」等資料夾的影像,似乎間接的給出對此的回應:自我技術。

白雙全〈噩夢牆紙(No.DCCC901–16#15):蛇吞熊圖〉
「假如⋯⋯的話」(If only…)強調了對過去的關鍵時刻及事件的回看、觀察、(再)處理,而這些動作會使當下與過去重新發生關係,白雙全以報紙作為媒介——或說「展場」——得以以作品之名讓報紙的「每日」加入不同時間軸,「過時」的議題仍可一次又一次借屍還魂成為「當下」;黃邦銓〈回程列車〉的拍攝源於爺爺一張未能寄出的照片,兩個世紀、兩趟橫跨歐亞大陸的鐵路之旅與兩個異鄉人被疊合在一起;致穎和Gregor Kasper的〈多哥咖啡〉(Café Togo)以虛構、重述及重演等手法揭開了柏林非洲區、街道正名及殖民宣傳電影等我們所不熟悉的德國殖民史。

Harun Farocki〈平行I-IV〉(Parallel I-IV)
「照這樣下去⋯⋯」(If this goes on …)句型則是使對當下的洞見擴增為對未來的可能描述,2014年世越號之後,韓國政治及社會上的病瘡被系統性地揭發,咸良娥(Ham Yang Ah)據此創作了〈睡〉及本次展出的〈未定義全景〉,試圖刻劃出社會上的支配結構;吳其育〈反覆驗證〉的創作基礎是驗證碼中「機器來判斷人是否為人」的弔詭機制,而在與人工智能互動的過程中,人又會有什麼樣的變形,甚至是與機器本質上的雷同;Kader Attia〈反映記憶〉(Reflecting Memory)以造成幻肢(phantom limb)的模仿慾望及對於完整主體的需求及想像起始,將此一病學名詞由個人的特殊病徵擴延為集體在面對歷史傷痛的常態;Harun Farocki逝世前的最後一組作品〈平行I-IV〉(Parallel I-IV)則以電腦遊戲的圖像及情節形成,回推人類透過科技來再現世界時所假設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常態」及「現實」;黃以曦以卡夫卡及波赫士筆下的世界投射出當下網路世界經驗,前者的世界作用於角色身上一如一比一的仿生模具,後者筆下世界中具體而微的套層結構,其實是看似無限的有限,角色的選擇則是假的自由意志。

黃以曦〈王國、城堡、迷宮與數位〉。(由兩場講演〈卡夫卡路徑:假性創造〉及〈波赫士現場:用有限消滅無限〉組成)
沿用Neil Gaiman的那句話,在本展中,此「尚不存在」的世界也就是共同生活的世界,正義不會淪為政客喊價之代幣的世界。假設語法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儘管看似指向未來,但若將預言內容作為檢核對象通常會是失準的,對於已經處在未來的人們而言,這些失格預言最準的反而是為了假設未來所進行的當下分析及運算,因此得以瞥見歷史事實之外的實在,而這也是黃建宏所說的「關乎『正義』的運算,因此是一種企圖逃脫各種潛殖支配的『運算』」。只不過,如同楊成瀚的擔憂:「作為當代『(轉型)正義 — (後)殖民 — (數位)科技』這三個極為重要的議題上行使的極為必要、迫切且有意義的槓桿,作為對這三角進行的轉動和連結,這個展覽對於一般觀眾的施力點、力矩和力道究竟何在?這恐怕是以任何形式實踐的「穿越正義」,在這個奇觀時代的最大挑戰。」(註2)在學科分類及實用主義之前,觀眾只有在「看起來很高科技」時才會覺得是「與科技相關的」;因此反烏托邦小說只會得到「對科技的想像不準確」的回應,而「穿越−正義:科技@潛殖」一展也只會得到「除了那條走廊跟自動書寫那件作品我不知道科技在哪裡」的反饋。在此,所遭遇的困難如同在平面國解釋立體為何(註3),但既然在最後,正方形能夠靠視覺以外的方式——「觸覺辨認技術」——以理性承認立方體的存在,姑且讓我們相信,仍然(且永遠)都會有人質問被認為已知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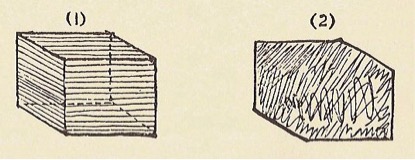
因為正方形處在平面國,因此它沒有能力「看到」完美的立方體,只能看到不規則的六邊形,而「不規則形」在平面國是有罪的。
註1:這個公司(或說這個世界)強調「所有知識屬於所有的人!不論何時!完全免費!」,此時代的圖書經紀員角色不再如舊世界的定義,他們的工作是查找所有紙本——從書本到單頁的筆記本廢紙都收——在掃瞄之後將其完全銷毀。總之,在未來圖書經紀員銷毀書,而消防員放火。
註2:楊成瀚〈沒有過去的過去和沒有未來的未來:《穿越正義:科技@潛殖》中的套疊結構和挑戰〉,刊於數位荒原。(http://www.heath.tw/nml-article/a-past-without-past-and-a-future-without-future/)
註3:《平面國》(Flatland: 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是由Edwin Abbott Abbott出版於1884年的中篇小說,儘管並不著重在未來世界的描述(因為所有角色都是幾何形狀),但有一個與反烏托邦小說相同的敘事線:主角由外面的世界學到了足以撼動本來世界價值觀的知識,當他想將此等頓悟經驗帶回該世界時,卻被以瘋子、異端制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