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景生活:世界主義的過去與中亞的未來
Author: [特約評論人] 鄭文琦, 2022年07月26日 21時26分
評論的展演: 《複景生活:當代藝術視角中的蒙古及中亞》特展
對於國族的依戀並沒有什麼自然或不言而喻的。反之,這些依戀是通過複雜的文化習俗和制度去建立、合法化和維持的。但是,與其要在當地社群或群體(⋯)之中尋找抵制民族主義和以國族為身份基礎的理由,這些理論家更傾向設法建立超越國族與遍及全球的文化想像和理解形式。(Ursula K. Heise)
 圖:《複景生活:當代藝術視角中的蒙古及中亞》二樓展場(右為曾建穎作品)
圖:《複景生活:當代藝術視角中的蒙古及中亞》二樓展場(右為曾建穎作品)
在〈複景生活:(自我)東方主義的拆解〉中,我們從中華民國臺灣與蒙古之間的歷史淵源出發,探討了《複景生活:當代藝術視角中的蒙古及中亞》(以下簡稱《複景》)如何披露東方主義的雙重視野,並以臺灣是否能夠承接中華民國與中亞地區曖昧的歷史遺產作結。但是,在觀眾無法對中亞地區的社會文化有更深理解的前提下,展覽各部組成相較於整體的時空不協調,可以說是一個折衷的結果。
在本篇裡,我們主要談到阿瑪古兒.門利巴耶娃(Almagul Menlibayeva)的〈烏魯柏格軌道.新絲路〉(Ulugh Beg Orbit. The New Silk Road in Space)。這件單頻道錄像被放在二樓的展場中央,全長半小時的影像充滿未來主義的視覺魅力。但是,這件作品顯然很難跟同樣位在二樓的相關主題作品—藝術家曾建穎以絲路石窟為靈感的〈本來無一物〉—相提並論。僅管我們可以說兩者都在探討當代藝術如何繼承進而超越共同歷史的遺產(絲路),但是兩者所採取的歷史或詮釋手法都截然不同。而〈烏魯柏格軌道.新絲路〉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在標榜「地方意識」(即中亞烏茲別克第二大城薩瑪爾罕(Samarqand)[1])的歷史記憶裡汲取出超越「地方/國家」格局的「行星意識」(sense of planet),而它所揭櫫的中亞未來主義,也提供了觀眾冷戰秩序瓦解之後的另類視野。
〈烏魯柏格軌道.新絲路〉這件錄像的主人翁,是建立蒙古帝國的征服者帖木兒(Timur)的孫子烏魯伯格(Ulugh Beg),他從1409年起統治帖木兒帝國的撒馬爾罕,並在1447年父親駕崩後繼任為帖木兒帝國蘇丹。他不僅僅是一位優秀的數學家和占星學家,還延攬了許多傑出的人才來薩瑪爾罕。而他建造的烏魯伯格天文台,更擁有當時全世界最大的觀星設備,經過30年驗證後於1447年編製出繼古代的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西元170年歿)之後第一個獨立的星歷目錄(包含了太陽、行星和1018顆恆星),更讓伊斯蘭天文學的成就在16世紀前達到巔峰。然而,綜合歷史對他的評價卻是:統御帝國的能力遠遠不及他在學術上的成就 。[2]
在一幕名為「我們如何管理我們的宇宙鄰里」的畫面標題拉開序幕以後,我們先是讀到一封由伊斯蘭學者Jamashīd al-Kāshī寫給他的父親的信。根據旁白口述,烏魯伯格邀請這位知名的學者來到天文台進行研究;而影像敘事則摻雜了傳聞與史實,包括天文台的構造(包括一座巨大的渾天儀),烏魯伯格驚人的記憶力,還有「將太陽的頻率化為聲音」等等情節。當然了,這座天文台不只見證人類智慧的偉大成就,更可以視為某種以行星為單位的基礎建設(這是用現代的觀念來理解)。當旁白打出「烏茲別克及塔吉克科學家之間,關於主要儀器的討論」這短暫的片刻時,我們似乎也可以想像不同民族的人們,為了追求宇宙真理而齊聚一堂的畫面。[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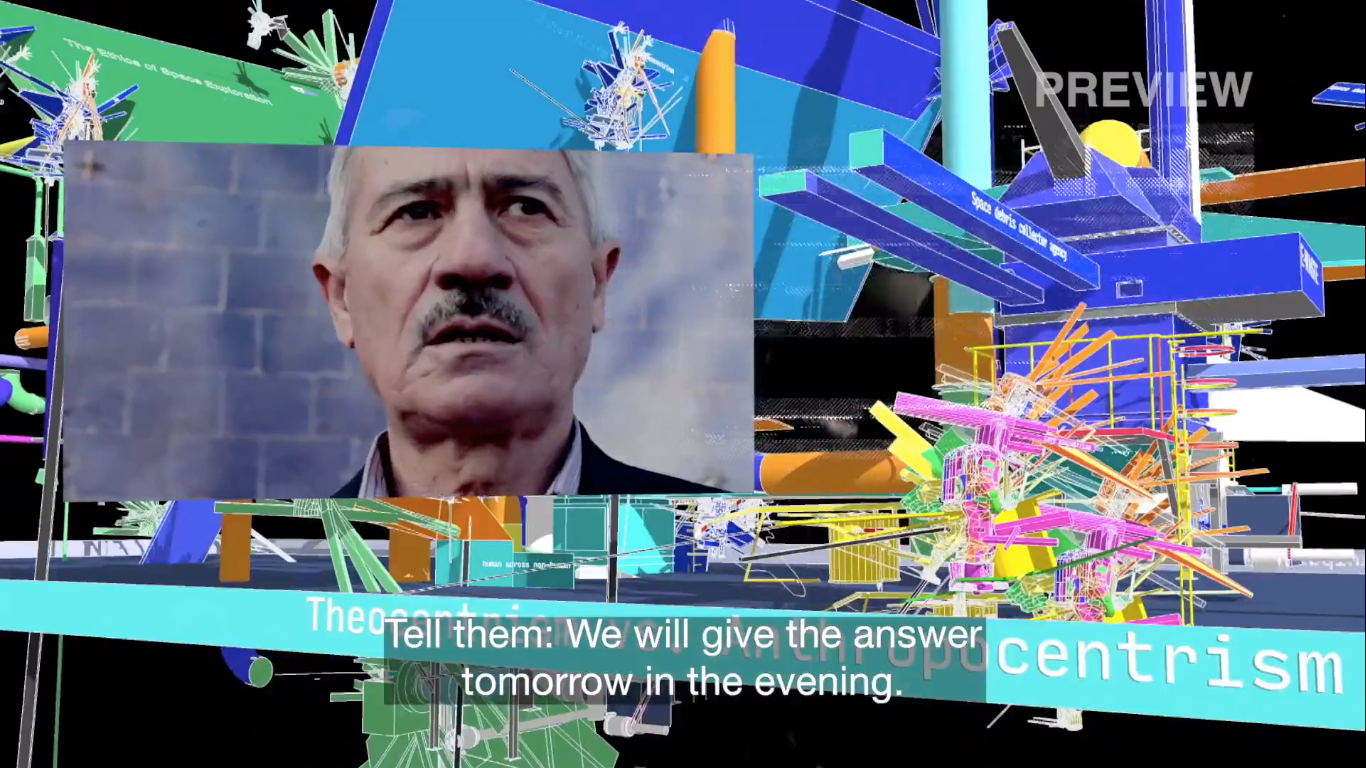 圖:Almagul Menlibayeva, Ulugh Beg Orbit. The New Silk Road in Space (2020)
圖:Almagul Menlibayeva, Ulugh Beg Orbit. The New Silk Road in Space (2020)
然而,這幅烏托邦似的景象並未維持多久,就被「太空外交VS軍事競爭」的標題給戳破了。雖然作品是奠基於史料上,但這裡的「軍事競爭」暗示烏茲別克鄰國哈薩克曾在前蘇聯太空戰略版圖上的拜爾科努太空發射場(Космодром Байконур)。一方面,(我們得知)烏魯伯格雖曾試圖對內征伐鞏固權力,卻被自己的長子Abdal-Latif Mirza所背叛。他也被迫退位,並在前往朝聖途中遭敵人以「背離伊斯蘭教義」的指控殺害。另一方面,透過這些破碎而零散的歷史再現,帝國的幽靈似乎也在旁白和充滿科幻感的向量動畫裡逐漸顯影了;畢竟烏茲別克罕和鄰近中亞國家雖然屬於遙遠的古代絲路,但藝術家2020年定下的標題「太空新絲路」(New Silk Road in the Space)卻更人想起「一帶一路」倡議最新的「太空絲路」(space silk road)修辭 [4]—暴露了影片最後,未來究竟偏向「人類中心主義」或「生態中心主義」的矛盾。[5]
關於本文一開始提到的「行星意識」,生態學者烏蘇拉.海澤(Ursula K. Heise)的文章〈From the Blue Planet to Google Earth〉(暫譯:從藍色行星到谷歌地球)或許可以提供我們理解如何從「地方」(中亞)轉向「行星」(太空)的線索。她首先引用勒規恩1971年的短篇〈比帝國更遙遠且緩慢〉(Vaster than Empires and More Slow)的描述指出冷戰期間「全球生態系統」概念的崛起,和這類對全球末日危機的道德呼籲如何轉化為處理當前危機的手段。但隨著全球化的程度因科技的進展而增加,越來越多環境行動者也改而強調「親近的倫理」(The Ethics of Proximity)這個「前現代的繼承物」(Zygmunt Bauman)。然而,正如鮑曼指出這種倫理其實反映了「以人類行動的範圍來衡量的空間距離(被科技)取消」,問題是它並沒有其他更令人信服的基礎,此外,由於「特定地點的特徵和歸屬方式都是由人類干預和文化歷史而非自然過程定義的」,人們也不應該對地方或民族傳統有著本質主義的預設。[6]
 圖:Almagul Menlibayeva, Ulugh Beg Orbit. The New Silk Road in Space (2020)
圖:Almagul Menlibayeva, Ulugh Beg Orbit. The New Silk Road in Space (2020)
海澤接著提到在1990年代後期,隨著對全球化的討論從社會科學擴展到人文學科,身份與各種空間關係的研究也將重點轉移到「跨國主義」、「批判國際主義」等概念上。此時「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也開始在各領域被恢復為一種想像超越地方和國家的歸屬形式的方式。誠如以下所述:
雖然這些理論家重新思考世界主義的方式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但他們與早期思考混種與離散的理論家卻有共同的假設,即〔⋯〕對國族的依戀並沒有什麼自然或不言而喻的。反之,這些依戀是通過複雜的文化習俗和制度去建立、合法化和維持的。但是,與其要在當地社群或群體(它們的流動性使其處於國族身份的邊界)之中尋找抵制民族主義和以國族為身份基礎的理由,這些理論家更傾向設法建立超越國族與遍及全球的文化想像和理解形式。無論什麼說法都關心一個問題:即我們要如何發展出與過去幾十年來政治、經濟和社會互聯的快速增長相稱的認同與歸屬文化形式。[7]
對於中亞各國來說,以民族主義作為抵抗全球化帝國收編的手段,或許是近代共同背負的宿命。然而,在夾帶著新型態、新技術與密集資本的帝國主義勢力再次來襲、且不斷以各種名義示好時,以「地方/國家」共同體作為基礎號召的認同,是否真能發揮凝聚共識之力?與此同時,從前現代到冷戰的歷史遺產或建設,又是否具有從「地方」到「行星」身份的一致性?雖然阿瑪古兒.門利巴耶娃以民族尊嚴書寫的「中亞未來主義」遊走在帝國連續史觀的險路上,但在考慮地緣政治和開發主義的泥沼之後,恢復「新絲路」作為行星尺度的基礎建設,是否值得人們做夢?無論如何,藝術家融合歷史文本與科幻製圖的敘事,都在「地方/全球化」的對立之外另闢蹊徑,也為中亞鄰國(或中國)的未來,注入更多「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的元素了。
註腳:
[1] 中亞以西至海、東到新疆,北到俄羅斯、南至阿富汗。根據長期占據中亞主要領土的前蘇聯定義,中亞指其五個加盟共和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薩瑪爾罕是中亞歷史名城與伊斯蘭學術中心。14世紀時為帖木兒帝國之都,目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它更是下文提及的烏魯伯格天文台所在地。
[2] 見維基百科Ulugh Beg詞條。亦可參考Kevin Krisciunas所撰寫的“The Legacy of Ulugh Beg”(烏魯伯格的遺產)一文。
[3] 作品第一大段幾乎都是在轉述這封信的內容,而諸多記載都提到了這封用波斯文寫的信件,在被翻譯成英文後成為決定現在關於烏魯伯格主要看法的歷史依據。如:Bagheri, Mohammad (1997). "A Newly Found Letter of Al-Kashı on Scientific Life in Samarkand". Historia Mathematica. 24 (HM962145): 241–56,以及Ekmeleddin İhsanoğlu; Feza Günergun (2000). Science in Islamic Civilis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a: "Science Institutions in Islamic Civilisation",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Turkish and Islamic World"
[4] BBC此前曾報導,北斗衛星系統的擴張與中國的對外政策相互結合;北斗衛星預計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為「太空絲綢之路」;可參考中國「一帶一路」網站。
[5] 關於中國如何在這條古代貿易路線上恢復帝國的疑慮,早在2016年就曾有國外智庫媒體將之與薩瑪爾罕的輝煌歷史相提並論。參考澳大利亞洛伊研究所《The Interpreter》的文章;RAFFAELLO PANTUCCI,“In Central Asia, China's New Silk Road stirs memories of over-reach and entanglement”。
[6] Ursula K. Heise, “From the Blue Planet to Google Earth,” eflux #50.
[7] “While there are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these theorists rethink cosmopolitanism, they share with earlier theorists of hybridity and diaspora the assumption that there is nothing natural or self-evident about attachments to the nation, which are on the contrary established, legitimized, and maintained by complex cultural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s. But rather than seeking the grounds of resistance to nationalisms and nation-based identities in local communities or groups whose mobility places them at the borders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se theorists strive to model forms of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at reach beyond the nation and around the globe. In one way or another, all of them are concerned with the question of how we might be able to develop cultural forms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hat are commensurate with the rapid growth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rconnectedness that has characterized the last few decades. ”出處同上,筆者自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