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要說是:陳曉朋2016個展「指鹿圖」
簡子傑 | 發表時間:2016/06/01 16:28 | 最後修訂時間:2016/06/01 1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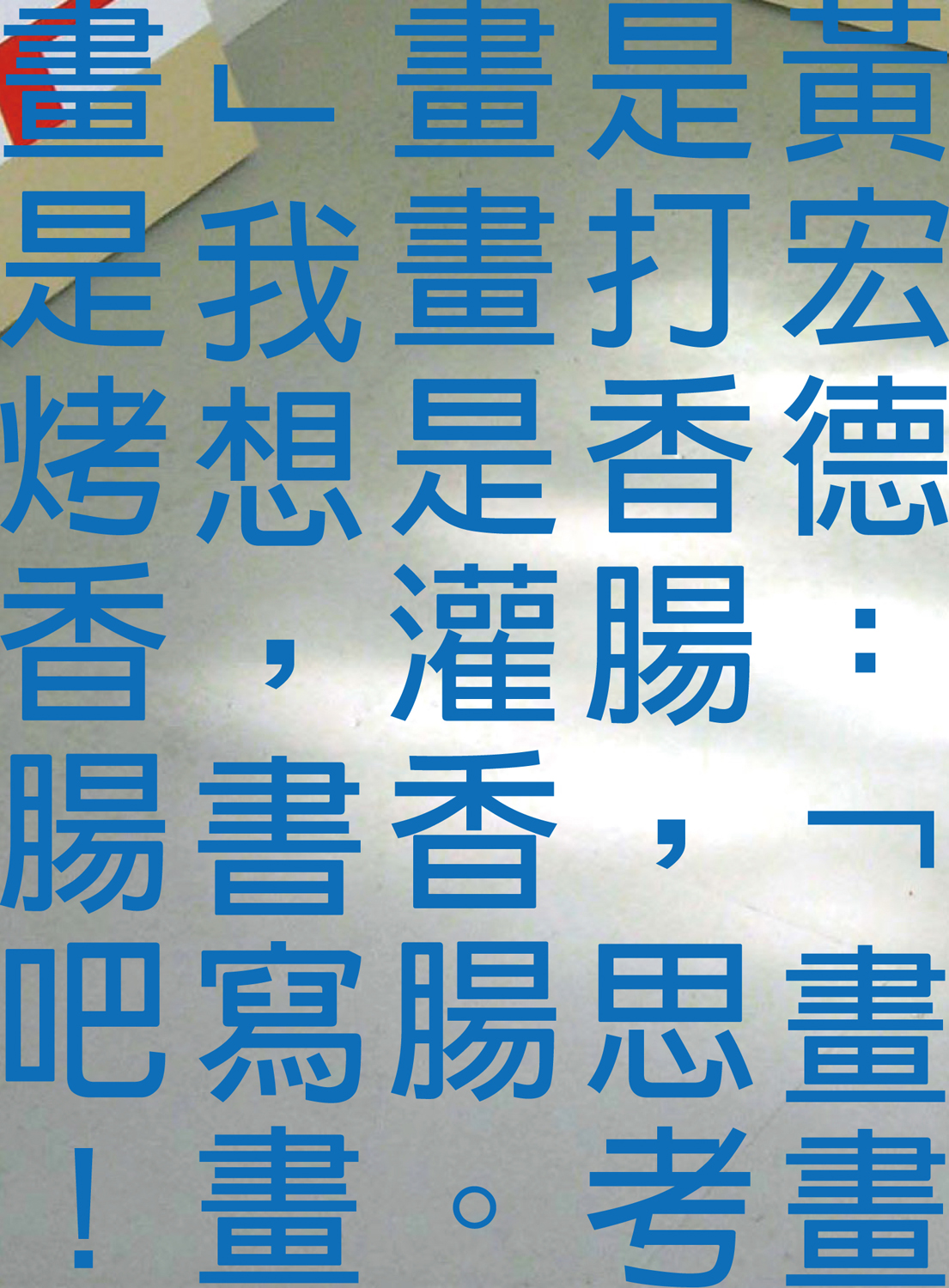
「我好想變成一個作家I」系列其中一圖,2013(陳曉朋提供)
陳曉朋在其個展「指鹿圖」的創作自述中說:「指鹿圖就是指路途」,儘管這種藉著同音異義以指向語言自身的手勢在現代藝術中並不算新奇,但相較於藝術家自行揭示了「路途」及其暗示的實踐姿態,從「指路」到「指鹿」的語意差異卻也表達了錯解之必然,這是因為,「指鹿為馬」之為路途很可能就是一種歧途,但這種不論是非卻硬要說是的態度卻讓我感到動容,尤其,在這個強調自反性、認識論、框架,以致藝術創作總是要把握什麼道理的年代,硬要說是不僅懸置了道理無所不在的存在感,也將「指鹿圖」導向創作者的主觀位置與其倫理結構——首先,我們必須了解陳曉朋過往的創作背景,如果說我們要在一位擅長賦予圖像以某種語法的藝術家身上見證法則並非難事,硬要說是卻更像是要在法則的合宜運用以外開闢另一種路徑,我將在這篇短文中試著描述這條陳曉朋路徑的生成模式。
首先,這個路徑看起來很關切藝術,但問題是先被從藝術家身份說起,陳曉朋提問的方式有點挑釁,她想知道除了當藝術家,可不可以讓自己成為別的什麼——在2013年的「我好想變成一個作家」系列的六件作品中,藝術家不僅直白地以文字覆蓋不知名的底圖,但除了從圖像轉向文字,「我好想變成一個作家」的題名更自爆了藝術家期盼獲得的另外一種身份——作家,這不乏無奈與自嘲的聲稱像是聚焦在藝術體制議題,卻也表達陳曉朋對於出路(exit)的欲求,我之所以名之為出路,是因為它們並非抽象的藝術理念,例如視覺藝術與文學的自主性爭論,而是帶著強烈的現實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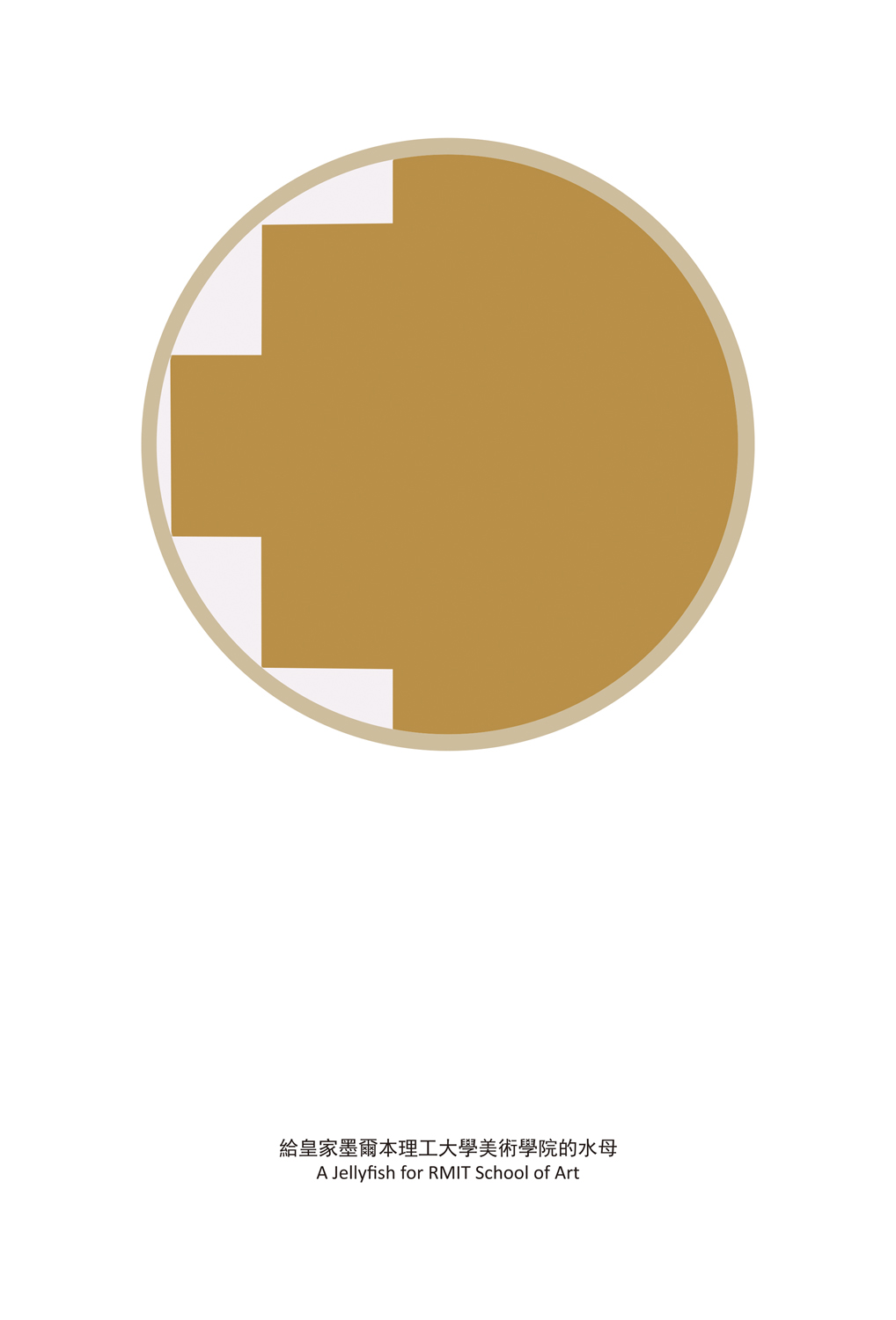
「獻給那些藝術家的禮物」系列中的《給皇家墨爾本理工美術學院的水母》,2014(陳曉朋提供)
在藝術家與作家之間擇選身份讓這個問題更像是在談職業選擇而非認同轉移,是生活方式而非抽象理念,於是這是個出路問題——如果我們想在當代藝術圈混出名堂,必須寫過無數篇的創作論述,成為作家除了揶揄了當代藝術有時過於空泛的論述要求,同時也迂迴地表達陳曉朋對於這種能力的渴望;再者,在2014年的「獻給那些藝術家的禮物」系列中,對其他藝術家的參照卻也形成了一套可疑的脈絡,陳曉朋很可能確實想藉著向藝術前輩致敬的姿勢連結出一個有著厚實基底的藝術脈絡——這份名單上確實不乏國際知名藝術家,卻也包含了令人莞爾的「給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美術學院的水母」,而當所有圖像皆來自她過去的作品,這就會是(另)一種為了攀附脈絡的硬要說是,但正因為硬要說是,這也表示陳曉朋並沒有忘記她獨特的現實感,透過黑白灰三色構成的《給傑斯波瓊斯的擴音器》其實很建立與現代藝術史間的脈絡連結,但這並非個別藝術家的問題,而是因為我們共同的被殖民處境。
另一方面,也因為是硬要說是,這也可能表示,即使我其實錯解了陳曉朋的意圖,但錯解之必然除了保障我身為藝評的言論自由,在現實與出路之間,我想強調,這種姿勢也為藝術家保留了替事物命名的權力:如果說在過往,這樣的權力專屬於詩人與神祈,在「指鹿圖」中像是鬼打牆般糾結的藝術家╱作家困頓,卻至少引出了陳曉朋的獨特腔調,我們讀著這些被裱框成畫的句子,看著一幅又一幅尺寸相同但上頭文字卻逐漸變大的圖像,只要一恍神就會將這些逐漸zoom in的文字看作符號看作線條,看待它們一如陳曉朋始終如一的繪畫形式,但它們同時又是洋溢著當代物性的印刷品,陳曉朋以詩人般的姿態將之命名為「我好想變成一個作家」。
陳曉朋的作品仍然擁有大寫形式主義意義下的現代主義樣貌,同時卻又擁有介乎文字、繪畫、版畫與出版物等多重屬性,而涉及觀念藝術傾向的命名走得卻又是完全不同於強調自反性的內省路線,而是更多地呈現出藝術家硬要說是的外部化姿勢,這樣的姿勢看似某種策略產物,但也正是因為硬要說是所隱含的現實感,陳曉朋在現實與出路間創造出的毋寧說是一種詩性,因為詩的語言不會是策略的,而是難以化約成別的什麼的所是,這裡的現實感因此帶著雙重屬性,就像在2015年「地圖集」系列中,這些形形色色的地圖雖可視為某種表現性探究,卻也是陳曉朋以藝術家之姿停留過的地點,它們一方面指向她無法忘情的地方性,再者,因為地圖本身不僅是通往另一個地方的鑰匙,地圖自身與其所指示的地點更形成了難以道盡的索引(index)關聯,在這份地圖上記載著統治者與非意願性移民都必須憑藉的出路,出路關乎現實,作為無可動搖的所是卻形構為詩。
「地圖集」系列中的《距離圖》,2015(陳曉朋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