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椰子樹的後殖民風景:從〈南方女人〉到〈剩餘的風景〉
鄭文琦 | 發表時間:2019/08/17 00:48 | 最後修訂時間:2019/08/27 18:25
評論的展演: 留洋四鏢客
扇子,女人夏天不可缺少的裝飾品之一。
像蝴蝶般一飄搖,女人就奇妙地看起來很活潑。
女人以各式各樣顏色的美麗的熱情,點描了南方剛毅的男性般的夏天。
南方豐麗的自然,給她們著色,而她們的清艷,給南方的自然著色。
光、光、光,藍色的是天空、椰子樹、椰子樹、
化妝的夏天女人,依偎著椅子,短暫的休憩。
啊啊。
讓婀娜的南方女郎,得到幸福吧。
—龍瑛宗,〈南方女人〉(〈南の女〉中文版,1943)[1]
共時的星叢
 圖:《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藝術時代》(黃亞歷、孫松榮、巖谷國士策劃)展場一景,國美館。圖片來源|鄭文琦
圖:《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藝術時代》(黃亞歷、孫松榮、巖谷國士策劃)展場一景,國美館。圖片來源|鄭文琦
在2015年,以南臺灣1933年成立的「風車詩社」為主題的實驗電影《日曜日式散步者》燃起本地對日治時期文學藝術的討論風潮。今年,導演黃亞歷與孫松榮、巖谷國士等台日策展團隊再次於國美館策劃《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藝術時代》特展[2],透過文學、藝術史與文獻的爬梳,呈現轉譯或在地的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地方主義,乃至於文學/劇場/音樂/美術或寫真等領域與戰爭、反殖、政治、歷史主題的辯證,重思20世紀初至1940年代西方到東方的現代性思潮及其與歷史關鍵時刻的交互作用。該展的獨特之處更在於,它一方面似乎指出過往夾在殖民與國族主義語境之間,我們有意無意地忽略政權交替所導致的發展斷裂(如「戰爭.政治.抉擇」子題)[3],另一方面也以跨界觀點探索作家們所屬的文學領域與不同藝術領域間的交互作用,使我們得以跳脫特定面向的侷限而綜覽藝術史全豹。
本文開頭這首名為〈南方女子〉的短詩(本文引用的版本是陳千武的譯法,收錄於前衛出版社《龍瑛宗全集》第六冊之〈南方女人〉標題),正是出自日治時期的客籍作家龍瑛宗所作的〈南の女〉。在這首詩裡,讀者除了可以看到詩人喜愛的夏天、南國、藍天或陽光等具有「熱帶風情」的意象,第五句尾的兩次「椰子樹」更是環境與人物間的重要元素,使閱讀的焦點從「南方的自然、天空」回歸到「夏天女人」身上。此外,《共時的星叢》也展出了龍瑛宗收藏的相關文獻;同樣印在《共時的星叢》展牆上的則是〈南方的誘惑〉,這裡我們又看到了椰子樹的身影:
在巴士海峽的遙遠彼岸,在陽光裡發亮著的呂宋島、爪哇島,以及那東邊的峇里島。豐饒的大自然,絢麗的民宿藝品,椰樹林的大月亮。煽情的音樂、浪漫的夜。我想起伊樊.歌爾的《馬來之歌》,和保羅.高庚的《大溪地紀行》。[4]
南方的風物
 圖:《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藝術時代》(黃亞歷、孫松榮、巖谷國士策劃)「戰爭.政治.抉擇」篇,左為陳澄波〈雨後淡水〉,國美館。圖片來源|鄭文琦
圖:《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藝術時代》(黃亞歷、孫松榮、巖谷國士策劃)「戰爭.政治.抉擇」篇,左為陳澄波〈雨後淡水〉,國美館。圖片來源|鄭文琦
上述這些在檔案櫃裡或在展牆上的資料,不外乎凸顯策展團隊的不同子題規劃,並將這些從日治時期跨越至民國時期、歷經不同國家認同的「臺灣」作家納入《共時的星叢》欲開展的戰前文學現代性光譜之中。在那段摘錄自1941年〈南方的誘惑〉的文字裡,「椰樹林」還連結了另一種「南方」的想像,其空間指涉延展至隔著巴士海峽與臺灣相望的呂宋島(比律賓,今菲律賓)、爪哇島,還有峇里島(荷蘭東印度,今印尼)」—在它們淪陷於打著「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口號的日軍手中以前。作者將「馬來之歌」與「大溪地紀行」並置的聯想,或許正是文人投射至帝國化外之邦的殖民地遐想。而椰子樹作為這些南方想像的共享地理特徵,生長在串連本地與東南亞的的殖民紐帶上,彷彿在形塑歷史的進程上扮演某種動力。
事實上,由於龍瑛宗筆下呈現多過於單一的「南方」意象,使其作品常常成為臺灣文學的研究主題[5],諸如臺灣作家的「南方書寫」如何回應日本「內地」盛行的「南進論」;台灣文學和日本受到歐洲影響的地方文學之間的關聯;更重要的是「南方」在這裡又有何意義?在龍瑛宗的詩與隨筆中,椰子樹作為一種熱帶風土的造型與象徵,頻繁地登場於1930年代晚期〈在南方的夜晚〉、〈花與痰盂〉到戰爭期間寫的〈東部斷章〉(1943)。除了椰子,檳榔、木瓜、番石榴、芒果⋯更是他常寫到的植物。隨著歷史從19世紀末到戰前,「南方」也指向日本的「東京以南」逐步轉向「南支(中國)」、「南洋」與「南進」,位於日本南方的臺灣風土,正好解釋了這些熱帶植物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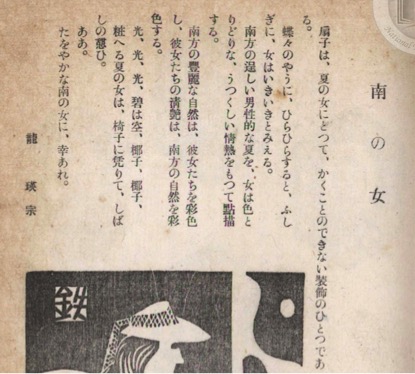 圖:龍瑛宗,發表於西川滿編《臺灣繪本》的〈南の女〉,1943。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圖:龍瑛宗,發表於西川滿編《臺灣繪本》的〈南の女〉,1943。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最近,高森信男在他策劃的《留洋四鏢客》(2019年7月20日至9月18日)展覽裡,邀請到藝術家李若玫的〈剩餘的風景〉系列之三(Landscape Remains – 03)。她在這個2016到2017年開始發展的計劃裡,以行道樹大王椰子為觀察對象,這也是她繼2015年於雪梨Artspace進駐的〈一些關於藍的研究〉裡的尤加利葉之後,再次以植物為主題的創作。同樣是在《留洋四鏢客》中,本地藝術家張恩滿研究的非洲大蝸牛,和馬來西亞藝術家符芳俊研究的吳郭魚,都是戰爭前後來自新加坡的外來物種。牠們從南方逆向輸入臺灣的遷徙路徑,正好逆反帝國的南向擴張;既呼應「人」作為主體的全球化流動過程,也勾勒出「人與物」互動下的多樣化文化景觀。
剩餘的風景
在展覽中,李若玫結合素描及紙模型製作,揣摩出「介於標本及寫生之間的特殊形體,並透過細膩的細節呈現出某種抽離的弔詭情境」(摘自展覽文案)。她以城市街景常見的大王椰樹造型為主題,進行材質上和視覺上的轉譯及立體造型的空間調度;這件作品所探討的特定對象,即大王椰子(Royal Palm或Cuban Royal Palm,學名Roystonea regia),其實是日本殖民者刻意引進、栽培的一種外來物種,臺灣人往往並未意識到。事實上,她的創作動機原本來自在淡水真理大學校舍磚牆上的挺拔樹影,「察覺在建築物牆上投射一半高度的椰子樹陰影」[6];這種臺灣特有的仲夏風情或南國印象,正如龍瑛宗的椰子樹總是連結著夏天、藍天和陽光的熱帶意象。
 圖:李若玫,〈剩餘的風景〉之三,TKG+(2019)。圖片來源|TKG+臉書
圖:李若玫,〈剩餘的風景〉之三,TKG+(2019)。圖片來源|TKG+臉書
那麼,這種印象又是從何而來,又是何時開始成為我們既定的夏天印象呢?根據資料,臺灣都市常見的大王椰子是1901年殖產局農務課技手今井兼次,從夏威夷帶回大王椰子種子於恆春熱帶殖育場育苗成功(因為1889年由御苑寄來的第一批種子失敗)。根據《日治時期臺灣熱帶景象之形塑:以椰子樹為中心的研究》的作者周湘雲,曾為殖民地留下眾多植物報告的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正是臺灣大王椰子的風土理論奠基者:
田代安定提出了一套行道樹理論,並認為行道樹是「社會的裝飾物」,反映出一國「文明」與「進步」的格調。田代曾經赴歐考察各國科學化的園藝知識與技術,並參考歐洲殖民帝國治理熱帶殖民地都市景觀的先例,提出臺灣的風土氣候相當適合「印度南洋行道樹流派」的行道樹景觀規劃。由於他觀察到他國熱帶殖民地常以椰科植物打造出優美的行道樹景觀,以及椰科植物具有極佳的抗風性,能夠通過臺灣每年颱風的考驗,基於植物學與園藝學基礎的科學判斷,田代認為椰科植物是可以積極引進的優良行道樹種。[7]
 圖:張恩滿,〈蝸牛樂園─前導篇〉,TKG+(2019)。圖片來源|TKG+臉書
圖:張恩滿,〈蝸牛樂園─前導篇〉,TKG+(2019)。圖片來源|TKG+臉書
雖然《留洋四鏢客》藉由「單幫客」、「背包客」、「外來入侵種」和「時間旅客」等跨國行動以及文化品味的塑造或建構,延伸《留洋四鏢客》裡探索的文化混血這類去地方性的主題,但在這裡「流動的」空間與前述的《共時的星叢》文本聚焦的、殖民或帝國擴張的特定空間指涉(南進、南方、南洋等),顯然是大異其趣。而在前者與後者之間,從「外來」到「本土」代表的大王椰子,剛好映照出這樣從流動到定向的空間指涉,如何緊扣著臺灣共同體的想像塑造進程而凝聚。就像是《共時的星叢》展出的廖繼春畫作〈有椰子樹的風景〉描繪1931年高雄車站前的椰子樹景觀—
 圖:廖繼春,〈有椰子樹的風景〉,1931。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圖:廖繼春,〈有椰子樹的風景〉,1931。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另一幅也收錄在1943年出版的《臺灣繪本》裡,立石鐵臣為西川滿描寫舉辦過1935年臺灣始政四十年博覽會的〈博物館〉一文設計的精美版畫,也描繪出博物館前(今館前路)兩排筆直的椰子樹。於是,我們看見外來物種創造的殖民風景,逐漸在1930年代之後的作家、畫家作品中,走向與本地認同共生的宿命⋯⋯
 圖|立石鐵臣,〈博物館〉插圖,1943。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圖|立石鐵臣,〈博物館〉插圖,1943。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南方的誘惑
透過「椰樹林」,龍瑛宗的〈南方的誘惑〉裡不禁觸發我們重新思考「呂宋島、爪哇島,以及那東邊的峇里島」裡的南洋嚮往究竟從何而來?這篇〈南方的誘惑〉書寫的時間背景正與戰爭緊密相連,它發表在1941年1月1日,接著在1941年底,日本發動突襲珍珠港的太平洋戰爭。在那之前,日本的國策影片〈南進台灣(1939~1940)〉已顯露覬覦南洋豐富資源的野心,並且前進印度支那半島。「南方」的視野從南國台灣開展到「外南洋」[8]。從1930年代「南進論」的確立時期和1936年宣布「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治台方針,「南方」的定位從帝國最南邊陲的臺灣,到1940年代擴大解放的「整片南洋」。[9]上述作品的「南方」語境,無不反映國際情勢的演變,與日本帝國對殖民地的「風土」景觀塑造,甚至本島作家也不掩飾東亞共榮理想的那份雀躍。
無論上述台灣作家與畫家的創作是否基於「人與風土不離」[10]的風土論主張,後者皆為殖民主義解釋人種優劣或地景現象的偽科學根據。經明治維新後,日本躍升進步國家之林,民智大開。為了印證亞洲的國家能充份克服熱帶人種、自然生態或海島環境的限制,在1895年終於從清國取得台灣這個絕佳的殖民開發和實驗環境,矢志開發台灣以證明日本轉型成功、打造不同於亞洲其他殖民地的進步典範。與此同時,從1901年引進的椰子樹、到1931年的高雄車站到1935年左右的總督府博物館入口行道樹,最後成為1943年龍瑛宗筆下的南國代表植物。雖然,這無疑鑄成日本軍國主義終至功敗垂成的關鍵第一步,但日本人所構築的南方想像,早已深入我們的文化記憶,最終如大王椰子的樹影一般,成為融入本地血脈的文化基因之一了。
註解:
1. 見《龍瑛宗全集》第六冊,前衛出版社。龍瑛宗(1911年8月25日~1999年9月26日)為客籍小說家、詩人,代表作為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南方女人〉原是以〈夏の庭、南の女〉的名稱共同刊載於《台灣繪本》,1943年1月28日。此處中文版陳千武譯自〈南の女〉部份。
2. 黃亞歷、孫松榮、巖土國士共同策展, 從2019年6月29日至9月15日,依主題分為「現代文藝的萌動」、「現代性凝思;轉譯與創造」、「素度趨使未來」、「超現實主義眾生迴響」「機械文明文藝幻景」、「文學—反殖民之聲」、「藝術與現實的辯證」、「地方色彩與異國想像」、「戰爭、政治、抉擇」、「白色長夜」於國美館101、102、201等三大展區展出。
3.見鄭文琦,〈旁觀他人之戰爭—在「情書.手繭.後戰爭」外的二三事〉,ARTOUCH(2019/8/13擷取),2019。
4.同樣收錄在《龍瑛宗全集》第六冊,前衛出版社。
5. 如吳昱慧,〈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南方想像」 : 以龍瑛宗為中心〉,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花木蘭文化),2013。
6. 張恩滿,〈藍色迷霧與歷史的植物學想像:論李若玫的創作〉(2019/8/16擷取),2018。
7. 周湘雲,〈景觀植物與熱帶南國景象─椰樹栽植〉,《臺灣學通訊》第80期/園藝,2014。
8. 先前作者曾有數篇文章提及「內/外南洋」與漢人使用「南洋」的語境演變,這篇文章或許可以提供不同的建議。洪偉傑,〈「南洋」指的是哪裡?關於南方想像,一個關鍵詞彙的身世之謎 〉(2019/8/16擷取)m2019。。筆者認為這些詞彙(南方/南支/南洋)的應用必須回溯到期時代、社會背景進行脈絡性的解讀。
9. 1914年8月日本對德宣戰,並在10月佔領馬里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與馬紹爾群島。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依凡爾賽和約委託日本統治南洋群島,日本於塞班島設置南洋廳。1933年退出國際聯盟,南洋群島成為日本直轄地。當時其正規劃以台灣為南進基地發動戰爭。這也告訴我們必須在思考「南進/南洋」歷史的去殖民背景下,重新定位臺灣與近代東南亞的關係—這些正是以日本美術館體系主導的《太陽雨》展覽昧於提及的去殖民關鍵。
10. 和辻哲郎1935年寫的《風土—人間學的考察》為1927年遊學歐洲、受到所海德格影響而對人與空間性的結構補充說明,「風土」一說常被援引為殖民治理論述基礎。臺灣與南洋皆被歸類於「季風」型。而人是否受限於風土或能超脫先天的限制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重點在和辻的風土是一種與歷史因素交涉的過程,如廖欽彬提到:「『人間』與風土現象的交涉,必與歷史性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人間的,也就是帶有個人與社會雙重性格知人間的自我了解運動,同時也是歷史的,因此,既沒有與歷史分離的風土,也沒有與風土分離的歷史』」)。見廖欽彬:〈和辻哲郎的風土論—兼論洪耀勳與貝瑞克的風土觀〉(2019/8/16擷取),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