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宏--不是療癒力,是感受他方的能力
Author: (080靈)通話藝術家, 2015年04月15日 12時45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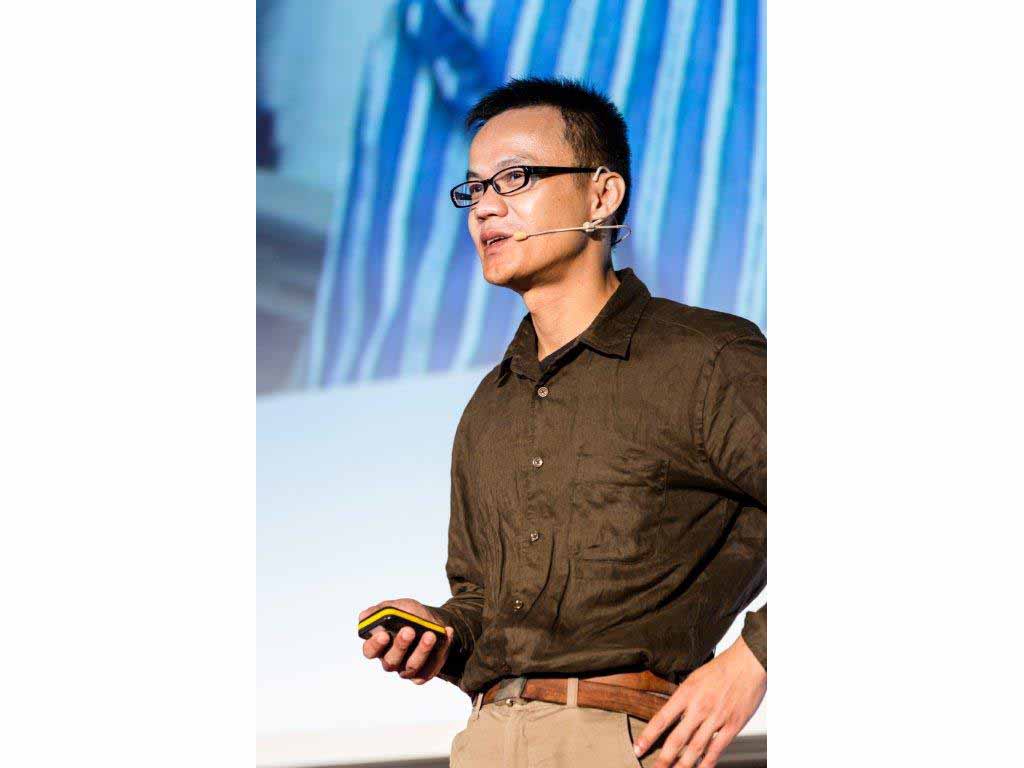
文字|林宛縈
Q1__如何定義「身心靈」?
A1__像陀螺一樣,需要一條線、一個外力才會轉。它以為自己是朝著自我中心在轉,但其實也是假設出來的。
Q2_藝術創作和身心靈的關係?
A2__藝術如果做一個身心靈的機器,那恐怕又是一個龐大的產業。
Q3__你認為藝術創作有療癒的功能嗎?
A3__很難說,也很難驗證。
Q4__對想走入藝術創作追求身心靈體驗的人有何建議?
A4__現在有人會夢想走進藝術創作嘛?我沒辦法想像耶!這條路真的還有人想走?
高俊宏的藝術創作一向帶有強烈的身體力行,早期作品光從字面上「追火車」「跑河堤」「跳啊跳」「丟雞蛋」「吃報紙」「嘔吐」,便能感受當中濃濃的身心煎熬。和他談身心靈,等同於一場人生與創作的大回顧,當中的分水嶺,是「山」。
他在學生時期開始積極參與藝術。前10 年,創作是信仰,「那時還滿超越的,好像遇到什麼現實上的困難,都還有創作。如果那時候談身心靈,我覺得是很自我、很Ego 的,就像西化教育中一直灌輸的那種『創作就是表達自己、說自己想說的話。』」
然而,當時篤信的「自己」到頭來也困住了他,2007年得到台新藝術獎後,他找不到創作方向,人生陷入大低潮,「對我來說很痛苦,可能還不到憂鬱症,但很焦慮。我以為自己脖子歪掉,跑去整椎、做倒吊治療,西醫、中醫、量子醫學……」正所謂心理影響生理,外加個病急亂投醫,「試了很多方法,整整一年都沒效果,也從沒睡飽過,狀況很糟糕。」
為了治療身體,或是說,解決創作上難解的自我懷疑,他開始強迫自己走進山裡,專走人煙稀少、路況險惡的郊山。講起他在山裡最害怕的,不是猛獸,也不是魔神仔,是嗜人血於無感的山螞蝗:「那種東西真是地獄來的魔鬼!我不懂為什麼台灣會有那麼邪惡的東西!它吸血時會分泌麻醉劑,讓人沒有感覺,一旦發現不能硬拔,因為一不小心它的嘴就會永遠留在皮膚裡,和你的身體結合。」
螞蝗只是其一,處於大自然無時無刻得面對的恐懼,還包括身體極限、斷糧危機、氣候驟變等狀況。在入山與出山之間,渴求生存讓他原本惡劣的身心狀態,逐漸化解、痊癒,「我是自己把自己給治好的」,他說。
也許是入山之後,求生必須全神謹慎地觀察四周,他清楚感受到自己有種「公共性」的能力被開啟。「我覺得很神奇,如果藝術要談公共性,不只是和社會運動合作,而是具備『感受他方』的能力。比如說,一個人坐在你後面,你可以知道他為何自己孤獨坐在那?他在睡覺,你可以知道他為什麼會那麼累?」
他也對「身心靈」產生了強烈批判,不再相信那些以自我為中心的身心論(諸如「把自己過好,調適好自己和社會、自然的關係,身心靈就能提昇」等概念)。他將視點移到讓陀螺旋轉的那條線和那股力,進而發現整個社會,或說是台灣社會大部分的人,其實都處於身心靈失調的狀態。
這轉變的過程中還有個關鍵,有次他在三峽的山裡走著,無意間進入廢棄礦坑,開啟了近幾年的廢墟計畫。「心靈改變直接影響到身體改變,我變得像隻狗一樣,跑跑跑到廢墟裡到處聞到處嗅,察覺到有一群人是被社會淘汰掉的失敗者。對我來說,廢墟的定義,就是個失能的空間,裡面充滿著失去的技能、被淘汰的人和產業。我希望在某個層面可以跟他們對話。」
「他們」,那些隱沒在荒煙蔓草中的失能、失敗之物,和其中散不去的不快樂,在高俊宏進入廢墟時,總是可以強烈地感受,「好像正在看一部看不見的電影。」面對這些無形的能量,他從唯物主義解讀,「 物質不滅,過去無法消失的意志留在原處,就和蝴蝶一樣是一種存有。慢慢的我可以接受那些感覺,我必須處理和碰觸的東西,不是鬼,是集體的遺憾、集體消失的世界。」
對他而言,在入山後開啟的公共感受力,是創作中最重要且天然的,「如果對藝術懷抱夢想,就必須要有這個能力,才不會像在坐牢,在藝術機器中打轉。」
從自我到公共,仰賴到懷疑,要說高俊宏的身心靈因入山被改變、重組、再定義,似乎也是身為一個聽者的片段的歸納解讀。可以確定的是,當他描述著在山裡獨自面對魔鬼螞蝗的恐懼時,你我都痛痛癢癢地感覺到了。





